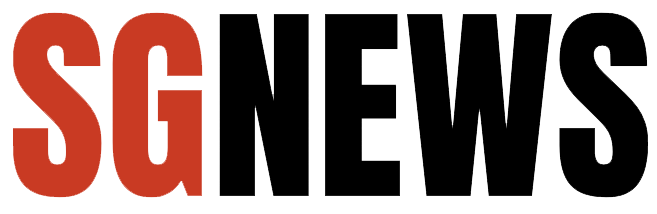路边的野菜随便采? 越来越多新加坡人爱上了野外觅食材
2024-04-16 月曦 3617
在魔鬼岛(Pulau Hantu)退潮时可以觅食蛤蜊。(海峡时报)
作者 侯佩瑜
在新加坡用不着野外求生,到处都有24小时的超级市场、便利店,为何会有新加坡人喜欢上野外觅食(foraging)呢?
再来,不是说“路边的野花不要采”、“草地上的蘑菇都有毒”,在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觅食会不会困难重重?
觅食指的是采集有用的动植物作为食物、药物甚至是艺术材料,这种远古时代野人的生活方式,竟在新加坡悄然复兴,尽管它仍然只是一种小众的兴趣爱好。
其实,在新加坡各地常见的草地、路边的树木和沙滩上,可食用的生物繁盛,只是大多数人没注意到,只有识货者才知道“遍地黄金”。
觅食向导、也是永耕设计师公司CarbonInQ创办人杨柏源说,
尽管市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觅食课程,竞争更加激烈,不过疫情过后,他的觅食班报名人数仍然增加了一倍。
39岁杨柏源从小常协助母亲照顾花草,大学毕业后在国家公园局从事道路景观工作,照顾树木。
后来,他到菲律宾农场当了八个月义工,回新后加入Edible Garden City当城市农夫,2014年创办社企Carbon InQ,除了用可食植物为客户造景,也教授自然教育。
杨柏源的上课地点,通常会在报读觅食课程学生住家附近,因为他想传达一个信息:食物近在眼前,就生长在家门外,在你的“嘴边”。
因此,他会带白领客户到办公大楼外的草地上或带一群学生在校园里“上课”。
他告诉《海峡时报》:
“杂草是最令学生着迷的,因为大家能认出它们,并说讨厌它们,但当他们知道这些所谓的杂草可以食用且对身体有益,或能用来愈合伤口时,他们顿时变得很兴奋。”
另一名觅食向导 Esmonde Luo(36岁)也说,
越来越多的不同群体(厨师、学生和办公室职员)邀请他开办80元一次的觅食课程。

Esmonde Luo正在进行城市觅食课程的讲解。Esmonde无师自通,自学各种野花野草。(Esmonde Luo)
两位向导皆认为,新加坡城市觅食的兴起,源于对食品安全的担忧。疫情暴露了供应链的脆弱性,成功地吓到人们,让大家开始对永续生活有兴趣,尝试在新加坡本土认识和寻找可食用植物。
但是,对“储藏室空无一物”的恐惧只唤醒了觅食者在野外觅食的欲望,这并没有转化为觅食者饮食的任何重大变化。向导估计,这些去上课的人,每天进食的食物不超过10%是通过觅食而来。
哪些野菜野花是可以食用的?
杨柏源也自费写了一本英文书:“101 Edible Plants——A guide to designing foodscapes in Singapore”(101种可食植物——在新加坡设计食事风景的指南),借此鼓励更多人尝试栽种和食用新加坡本地植物。
他说,这个大自然“菜市场”并不是很稀有的,譬如马来人本来就有觅食的习惯,会采摘Ulam(马来人的生菜沙拉统称),华人则偏爱采摘中草药猫须草(Cat's whisker)。

猫须草——又名肾茶。在某些东南亚地区被用作草药饮料,也称“爪哇茶”。民间传统医学以之调理尿结石、糖尿病和高血压。不过中医认为,有肾脏问题者须谨慎食用,因在实验的动物中发现猫须草可稍提高肾脏功能酶,造成轻微肾损伤。(联合晚报)
杨柏源最爱的是紫花酢浆草(Lavender Sorrel)、野胡椒以及小叶冷水花(gunpowder plant),因为这些都是新加坡随处可见、生命力很顽强,含有益健康的植化素的植物。
觅食向导Esmonde则以野外采摘的罗比梅(Rukam Masam)酿了一瓶梅酒,据他描述味道就像日本传统梅酒umeshu。

红蚂蚁来自缅甸的女佣也会经常指著野草、野果、兴奋地告诉我们,这些植物的药用有多好、味道多美味。
譬如以下的崩大碗(Pegaga)。

崩大碗(Pegaga)。(红蚂蚁提供)
崩大碗性寒凉,广东人喜欢用来煲凉茶降火消暑。不过红蚂蚁的女佣喜欢直接当作沙拉食用。
未完待续,请点击[下一页]继续阅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