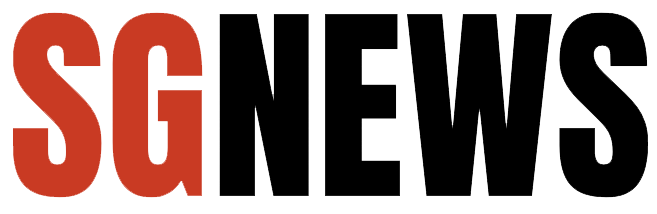“看了很多场昆曲《牡丹亭》,新加坡的版本更素雅宜人”
2024-04-19 缘分 3159崇祯二年(1629年)中秋节的后一天,我的老乡、明代散文家张岱经由镇江前往兖州。船停岸时,张岱在《金山夜戏》里写道,林下漏月光,疏疏如残雪。他趁著兴致走进暗影绰绰的寺庙大殿,让仆人把唱戏的工具带来,在大殿里盛张灯火,锣鼓喧阗。戏文唱完了,天也快亮了,张岱携仆人收拾行头,行船飘然而去,独留被吵醒的众僧人目瞪口呆。
金山夜戏,湖心亭赏雪,“莫说相公痴,更有痴似相公者”。人生如一场大梦,张岱是明末浙江山阴人(今浙江绍兴),“少为纨绔子弟、极爱繁华”,后又是“年至五十,国破家亡”隐居山野的前朝遗老。《金山夜戏》里,张岱唱的是“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”,但我未找到他具体唱的是哪一个剧种,我盲推可能是绍兴戏。
一个地方只有拥有多元的文化,才能孵化出迥异风格的地方戏。绍兴便是这样一个奇怪的地方,既出高亢的绍剧,又有柔媚的越剧。绍兴戏源于秦腔,原来叫“绍兴乱弹”或“绍兴大班”,音调高亢激越,旋律节奏急速明快,声音清越刚劲,擅长表达悲壮、慷慨激昂的情感,唱白通俗易懂,表演风格粗犷豪放,或可如梅花,宁可枝头抱香死,何曾吹落北风中。
丝不如竹,竹不如肉。
张岱所在的明朝末年,江南的戏剧发展俨然达到了顶点,特别是源于14世纪中国苏州昆山的昆曲,自明代中叶以来独领中国剧坛近300年。因为这种腔调软糯、细腻,好像江南人吃的用水磨粉做的糯米汤团,因此还有一个有趣的名字,叫“水磨调”。

昆曲以一种纷 繁富丽的表现形式向人们展示著世间的万般风情,是当时江南富绅趋之若鹜、附庸风雅的最爱。我愿意把昆曲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剧作家之一汤显祖,比喻为“东方的莎士比亚” ,他比莎士比亚只大15岁,当莎士比亚的《仲夏夜之梦》以其旖旎浪漫在伦敦剧院里的贵妇人中间风行时,汤显祖《牡丹亭》里绮丽的闺门幽梦正在苏州园林里的戏阁里引发如痴如醉的迷恋。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,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,死而不可复生者,皆非情之至也。
及至今日,《牡丹亭》《桃花扇》和《长生殿》依然是昆曲里最受欢迎的曲目,4月10日,“相约狮城 遇见苏州”文化周在新加坡滨海艺术中心正式开幕,其中一项最为戏迷所期待的盛事是,苏州昆剧院的老师们带来了昆剧青春版《牡丹亭》精华本演出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迄今20年,而主演柳梦梅的依然是俞玖林,饰演杜丽娘的还是沈丰英,在戏里,他们依然是美的,执一支黑色墨笔,轻描浅放,勾勒出飞扬的鬓角,一抖袖、一折袖、一翻袖、一扬袖、一绕袖,动作舒缓,宽大的素白长衫,走起路来,衣身一甩一甩,空气在弧线的流动中,扬起一尘似有似无的性感。

在戏外,从20多岁走 到40多岁,他们承载了和我们一样的年华,和我们一起在成长、在变老,和我们一样有了家庭、有了儿女。 也正因这一种并不遥远的可以共情的持久的陪伴,他们也便带上了熟悉的带了一些感动的岁月滤镜,和我们竟可以一直呆在《牡丹亭》的梦境里,从苏州到北京,再到新加坡,关于临川一梦的青春记忆,是可确定的、可被触摸的,是一直在那里的。
2004年,江苏省苏州昆剧院与著名作家白先勇携手共同打造昆剧青春版《牡丹亭》,迄今已在海内外60余座城市演出近500场。青春版《牡丹亭》将原著浓缩成27折,分为“梦中情”“人鬼情”“人间情”上中下三本。当时,俞玖林因为一次讲座上的一折《惊梦》,白先勇先生认定他就是青春版《牡丹亭》中的“柳梦梅”,并拜“巾生魁首”汪世瑜老先生为师。
一年后的4月,白先勇携青春版《牡丹亭》首次来到北京大学连续演出3天,我从宿舍前往理教上课时,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盛景,购票的人群从讲堂门口排到了三角地,一票难求。演出时,北大百周年纪念讲堂剧场2200多个座位都被早早占满,“走廊里、墙角边全是人,晚上11点很多人还没散去。”叩板响起,俞玖林已成了柳梦梅,他缓步穿越幕布,甩头侧望,眼神流转,折扇在手里一开一合。转身、站定,浅吟低唱《山桃红》里的阙词,“则为你如花美眷,似水流年,是答儿闲寻遍,在幽闺自怜”……满场喝彩声。

另一厢 ,沈丰英的杜丽娘幽幽吟咏“似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,生生死死随人愿,便酸酸楚楚无人怨”,及至旁白“情不知所起,一往而深,生者死可以死,死可以生”……台下那些穿着文化衫、长著青春痘的年轻人们癫狂地喝彩,有的还湿了眼睛。
一位外语系的师兄恰好多了一张票,便送给我看了上阙,后来我又想办法买到票看了中阙和下阙。每年的4月,正是毕业季人来人往的时节,恍惚想起来,倒是青春易散的颜色。再后来,我毕业了,在一家体制内大报写特稿,当时的主编派了一个昆曲的选题,我便抢著去了。
采访的正是,《牡丹亭》的顾问、俞玖林的师父、曾经的“巾生魁首”汪世瑜老先生。他的大半辈子都在唱昆曲,后来,他不再美了,老到无法抵抗时光,身体开始发福,眼角长出了皱纹,脖子上还有零星的老年斑,他的名字不再闪烁在霓虹灯管上,他的剧照消失于烫金的演出海报里。
可是,他终究还是美的,他就是《春江花月夜》里的张继华、《牡丹亭》里的柳梦梅、《桃花扇》里的侯朝宗、《长生殿》里的李隆基,他的美就在发黄的唱片里,在昆曲迷珍藏的故纸堆里,在岁月纠结的齿轮里,一圈一圈地回寰、咀嚼、升华。
未完待续,请点击[下一页]继续阅读